在长江上游的崇山峻岭间,有一支以忠勇为血脉、以信义为骨骼、以开放为气度、以包容为胸怀的古老文明,它如蜿蜒的巴水般浸润着西南大地,历经三千年的风雨沧桑却始终保持着独特的精神品格。这就是以“忠勇信义,开放包容,认同中华,崇尚统一”为精髓的巴文化。从武王伐纣的战场到汉唐盛世的宫廷,从青铜兵器的虎纹图腾到“巴蜀图语”的神秘符号,巴文化始终以刚毅与灵动的双重气质,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。
一、忠勇信义:熔铸巴人的精神脊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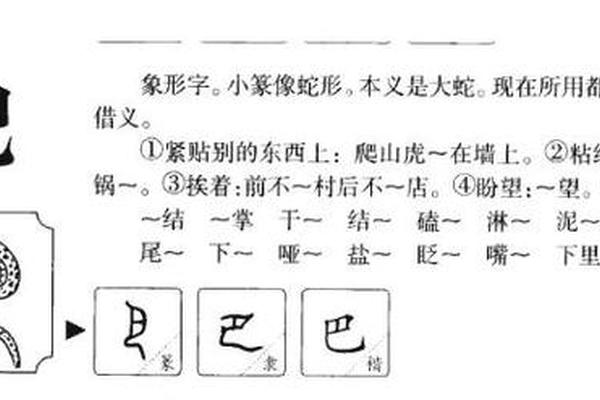
巴文化的忠勇基因深植于族群的血脉记忆之中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的巴蔓子将军“刎首存城”的壮举,将“忠”推向了以身殉国的极致境界。当楚国使臣索要承诺的三城时,这位巴国统帅以头颅践行诺言,其头颅在楚地以诸侯礼下葬,身躯在故土享受同等尊荣,这种超越生死的精神图腾,成为巴文化忠义品格的永恒注脚。在罗家坝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上,密集的戈、矛、剑、钺等战争器具占总出土文物的七成以上,印证了《尚书》所述“巴师勇锐,歌舞以凌殷人”的史实。
这种尚武精神并非野蛮的暴力崇拜,而是蕴含着深厚的准则。商周青铜器上的虎形纹饰,既是“巴人崇虎”的图腾象征,更是军事信义的物化表达——虎纹兵器在部族盟誓中作为信物,维系着军事联盟的神圣性。从甲骨文中“王比奚伐巴”的战争记录,到战国时期巴楚会盟的青铜铭文,忠勇信义始终是巴人处理族群关系的核心准则,使得这个山地民族在列国纷争中始终保持独立品格。
二、开放包容:构筑文化的共生生态
巴文化的开放性在罗家坝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该遗址出土的陶器既有嘉陵江流域的折沿深腹罐,又包含楚式高柄豆、蜀地尖底盏等外来器物,印证了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与楚、蜀文化的深度交融。特别在M83贵族墓中,龟甲占卜器具与楚式青铜礼器共处一室,既保留了“巴人尚巫”的传统,又吸收了中原礼制文明的精髓,形成独特的文化复合体。
这种包容性在精神层面更具创造性。巴蜀图语中的太阳纹、云雷纹与三星堆神鸟纹饰的相似性,揭示出巴人对古蜀文明的借鉴;而《华阳国志》记载的“秦巴会盟”,则展现了巴文化与中原政治智慧的交融。正是这种文化兼容能力,使得巴人在迁徙过程中,将汉水流域的农耕技术、三峡地区的盐业开发、川东丘陵的丹砂冶炼等多元生产技术整合创新,创造了“巴盐古道”“丹砂之路”等经济文化通道。
三、认同中华:奠定文明的融合根基
巴人对华夏文明的认同,始于武王伐纣时“前歌后舞”的盟誓,深化于秦汉时期的制度整合。商周甲骨文中“巴方”的记载,表明其早期作为独立方国存在;而《左传》记载的巴子使韩服聘于郑,则显示出春秋时期已自觉践行周礼。这种政治认同在器物文化上表现为渐进演变:战国早期的柳叶剑保留着巴式虎纹,至秦汉时期逐渐转化为中原制式的环首刀,纹饰中开始出现云气纹等汉文化元素。
文化心理的认同更体现在精神层面。巴人神话中的“廪君掷剑”“盐水女神”等传说,与华夏创世神话形成叙事呼应;《山海经》记载的“巴蛇吞象”故事,通过《楚辞·天问》的转译融入中华文学传统。这种深层的文化认同,使得巴地在秦汉之后迅速融入华夏共同体,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中“賨人劲卒”成为国家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,唐代巴渝舞更升格为宫廷燕乐。
四、崇尚统一:锻造历史的向心力量
巴文化对统一价值的崇尚,在地缘政治中转化为“王业之基”的历史自觉。秦灭巴蜀后,“得蜀则得楚”的战略价值,使巴地成为中央政权控制西南的枢纽。刘邦以汉中为基地平定三秦时,巴人“板楯蛮”组成的军队成为汉军主力,《后汉书》记载其“俗喜歌舞,高祖观之曰:此武王伐纣之歌也”。这种政治智慧在明清时期发展为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潮中的文化整合,巴地特有的“五方杂处”社会结构,反而催生出更强的国家认同。
在文化整合层面,巴人对统一的追求表现为符号系统的主动融合。战国晚期巴蜀图语中的“手心纹”逐渐简化为秦汉篆书的笔画元素,巴式印章开始出现汉字铭文。这种文字演进不仅是书写技术的改进,更是文化主体意识的升华,为西南地区融入中华文明体系铺设了精神桥梁。
站在罗家坝遗址的考古探方前,凝视着青铜剑上斑驳的虎纹,我们更能理解巴文化精髓的现代启示:当忠勇信义铸就文化自信,当开放包容拓宽文明胸襟,当认同中华凝聚精神共识,当崇尚统一锚定历史方向,古老文明就能在时代浪潮中永葆生机。未来的研究应当聚焦三大方向:通过分子人类学研究厘清巴人族群迁徙脉络,运用数字人文技术破译巴蜀图语符号系统,借助比较文明视角阐释巴文化在“多元一体”格局中的特殊机制。唯有如此,方能真正读懂这部镌刻在大巴山岩壁上的文明史诗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