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24年启动的“大地流彩——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”中,农业农村部与中国文联以文化铸魂为核心,将农民公益培训、乡村大讲堂等活动作为重要抓手。这些项目不仅传授农业技术,更注重在田间地头弘扬中华传统美德,例如通过“粮安天下”农民公益培训,将南泥湾精神、红旗渠精神等红色基因融入现代农耕教育,培育出兼具技能与文明素养的新时代农民。数据显示,2024年全国累计开展农民诗会、村舞展演等文化活动逾千场,直接参与农民达350万人次,构建起覆盖乡、县、市的三级文化传播网络。
这种文化浸润策略打破了传统单向灌输模式。正如南京农业大学仇童伟教授指出:“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尊重农民主体性,将道德教化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实践。”在河北滦平县花楼沟村,《守望长城的农民摄影师》项目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——村民通过镜头记录长城文化,既传承历史记忆,又衍生出摄影研学、民宿经济等新业态,形成文化自觉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循环。
非遗活化:传统技艺的创造性转化

“大地流彩”工程对非遗资源的挖掘保护具有里程碑意义。全国乡村记忆工程系统梳理出200余种濒危非遗技艺,建立数字化档案库,并启动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工作。山东省明一村将胶州秧歌与海阳秧歌创新融合,加入说唱元素后,《大美山东我的家》在抖音平台获得超5000万播放量,证明传统艺术完全能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。
这种转化遵循“保护中发展”原则。云南老姆登村将国家级非遗达比亚琴演奏与乡村旅游结合,开发的《老姆登之夜》文化体验项目,使村民年人均收入从2019年的不足3000元增至2024年的2.3万元。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评价:“当非遗技艺从博物馆走向市集、舞台、直播间,就完成了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质变。”这种活态传承模式,使全国乡村非遗产业规模在2024年突破1200亿元,年均增长率达18%。
教育赋能:构建多维文化育人体系
乡村教育文化空间的建构呈现立体化特征。农业农村部联合教育部实施的“文艺赋美乡村”行动,在全国建立150个乡村文化传习所,开展200期专题培训班,培育出3.2万名“乡村文化带头人”。重庆发布的全国首张乡村文化数字地图,整合287个特色文化点位,通过VR技术实现“云游乡村”,让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直达田间。
这种教育创新突破传统课堂边界。北京师范大学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发现,参与“村跑”“村BA”等活动的青少年,其文化认同感提升42%,辍学率下降至1.3%。在浙江安吉,竹编技艺进入中小学必修课,学生创作的竹艺作品在米兰设计周获奖,印证了“劳动教育+文化传承”模式的可行性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强调:“我们要培养既能读懂《齐民要术》又会操作无人机的复合型乡村人才。”
产业融合:文化要素驱动经济振兴
文化要素正成为乡村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。2024年乡村文化产业创意大赛涌现出1.3万个项目,其中福建武夷山《请到武夷来吃茶》茶舞衍生出的沉浸式茶旅,带动当地茶农收入增长65%。这种“文化+”模式在宁夏村BA赛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:赛事周边开发的胡麻油、枸杞等“村味”产品,单季销售额突破800万元,形成“一场球赛带活一条产业链”的乘数效应。
政策层面也在强化制度供给。中央《乡村全面振兴规划(2024-2027)》明确提出“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利益共享机制”。安徽宏村通过徽派建筑IP授权,年获得文化特许经营收入超2亿元,其经验已被写入《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指导意见》。这种产融结合模式,使全国乡村旅游总收入在2024年达到1.2万亿元,文化要素贡献率占比提升至34%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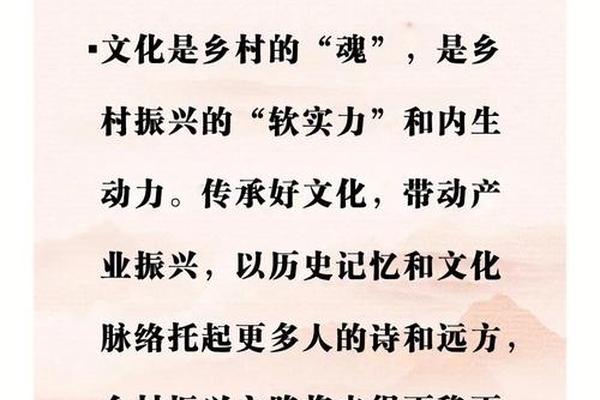
迈向乡村文化振兴新纪元
“大地流彩”工程通过文化铸魂、非遗活化、教育赋能、产业融合四维发力,构建起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国范式。数据显示,2024年全国乡村文化服务满意度达89.7%,较2020年提升22个百分点,印证了“以文养德、以文化人、以文兴业”战略的科学性。
未来需在三个方面深化探索:其一,建立乡村文化价值评估体系,量化测算非遗技艺、民俗活动的经济转化效率;其二,构建城乡文化要素对流机制,如北京平谷试点的“文艺村长”制度,已吸引127名艺术家驻村创作;其三,加强数字技术应用,借鉴“乡村文化元宇宙”实验项目,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文化资产确权与交易。正如农业农村部唐珂司长所言:“当每个村庄都能讲述自己的文化故事,乡村振兴就拥有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。”这场始于文化自觉的振兴实践,正在书写当代中国最动人的乡愁史诗。


